发布时间:2018/12/13 浏览次数:1184

尼古拉斯·雷诺兹
海明威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是美国《堪城星报》的记者,一战中红十字会救伤队员,他还是代号“阿尔戈”的苏联间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1940 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美国作家者尼古拉斯·雷诺兹试图在我们面前呈现一个更完整的海明威。他为何会和斯大林的“爪牙”签约?间谍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和生活?是什么导致他最终选择自杀?他的小说究竟是虚构,还是来自那些不能公开的真实经历?丧钟究竟为谁而鸣? 本文节选自雷诺兹的新书《作家、水手、士兵、间谍》的第四章,“丧钟为共和国而鸣:海明威见证了历史”。
到 1939 年 2 月初,佛朗哥的军队占领巴塞罗那后,数万名共和军士兵、随军流民和同情者走在从北面和东面出城的公路上,避开正在城中为胜利狂歌痛饮的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只要看谁像共和国的人,就不由分说地开枪射击。那些双车道公路其实更像乡间小路,有尘土飞扬的路肩,路上挤满了难民,有的搭乘轿车和卡车,有的步行,还有的坐在驴背上。农妇们赶着鸡牵着羊;母亲们领着孩子,人群涌向法国的避难所。
几辆卡车载着法西斯的飞行员,这些是俘虏,不知为何仍在共和国空军的手里。那些飞行员和他们的敌人互相辱骂,发誓彼此不共戴天,诅咒对方下地狱。但大部分共和军士兵都安静有序地行军。在即将越境进入法国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最后一次整顿队形,继而由几位军官进行了一次小型阅兵仪式,军官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安德列·马蒂。随后,士兵们把自己的步枪扔在成堆的武器装备中,任其凌乱地散布在西法边境西班牙这边的石头地面上。有些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国际纵队队员向前靠拢,唱着歌挺进法国。听到法国宪兵命令他们安静,喝道“禁止唱歌!”时,他们感到阵阵凉意。
作家海明威在基韦斯特读到了共和国濒死挣扎的消息。他的心仍在西班牙,但已经接受了共和国末日将近的结局。他的态度就像第一个从战场归来的退伍老兵那样,听到自己的同志们仍然手持武器在战斗,感到既愤怒,又内疚。有些记者报道赤色分子的暴行,或者声称佛朗哥一方更加人道(这当然是歪曲事实,但不止一个知名记者这样报道),令他怒不可遏。在写给岳母(鲍莉娜·菲佛的母亲,海明威虽然已跟玛莎·盖尔霍恩浓情蜜意,但仍对鲍莉娜的母亲充满依赖)的信中,他说那些指控根本不是事实。

1918 年的海明威
他见过“一个个城镇被炸成平地,居民横死,路上成群的难民一再遭到轰炸和机关枪扫射”。那是“一种摧毁内心一切信念的谎言”。想到他的好友们还身处战火最炽之地,他简直无法忍受,早知今日,真不如和他们并肩待在一起。他接着说,他“整个战争期间,在西班牙的每晚都能安然入眠”,饥饿时时伴随,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最后说,“人的良心很奇怪,它既不受安全感的驱使,也不被死亡的威胁所控制”。一天后他写信给麦克斯·珀金斯说他“每晚噩梦不断……那确实是些可怕的梦,可怖的细节清晰可见”。这很奇怪,因为他在西班牙从未做过噩梦。
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政治的看法。他仍然因为民主国家袖手旁观、任共和国自生自灭而悲愤不已。西班牙“以不同的方式被出卖和背叛了十几次”。在他看来,英国仍然是头号大恶人。他还在宣传他的戏剧《第五纵队》,该剧主旨就是为实现反法西斯的目的,可以动用残酷的手段。纽约的制作人们不急着上演这部戏,原因恐怕是“这场战争变质了”,但海明威仍希望把它搬上舞台。“哦天呐,我多么希望我当时把它写成小说”,他对珀金斯说。然而当时身陷战局,他没有时间写小说。
党的路线向来教条武断、自以为是,仿佛只有一种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从来没有为微妙情感或个人解读留有太多余地,但大多数党员都能够聚焦一两个投其所好的基本路线,例如反法西斯。如今,党突然推翻了这一核心教条,并要求忠诚者们捍卫这一变化。这样的逆转把诚实的男女变成了说谎的人。
对于四分之一的美国共产党员来说,这太过分了,他们彻底放弃了这项运动,再也没有回头。其中有些是文学人物,像曾担任《新群众》编辑的格朗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他几乎迫不及待地以低调而知性的方式解释他何以离开组织。他被党的独裁宣言所震惊,觉得他们“完全丧失了清醒和逻辑……如果党的领袖们无法明智地捍卫苏联,就必然会以愚蠢的方式来捍卫这个国家”。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剧照
另一个重要的叛逃者是海明威的朋友、人道主义的政委雷格勒。起初他无法相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份单独的协议。也许这只是又一次不负责任的空穴来风?看到报纸后他才相信那居然是真的。和希克斯一样,雷格勒也无法坦然接受党如今的双重标准思想。曾有一位共产主义医生声称该条约阻止了“真正的战争的爆发”,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签署的, 雷格勒无法苟同,虽然那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坚强的行医者。
海明威怎么看待苏德条约?雷格勒的书中有几处暗示。西班牙内战之后,雷格勒和海明威仍是好友。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海明威在 1939 年和 1940 年尽其所能地帮助雷格勒,共和国崩溃之后,雷格勒成了难民,海明威一直往法国寄钱给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海明威又发动舆论将雷格勒从愚蠢的敌侨集中营中释放出来。雷格勒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朋友,除了海明威,他的友谊坚如磐石。”最后法国人终于释放了雷格勒,他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又到达墨西哥,他和妻子在那里靠绘画和写作勉强度日,他们的作品非常有趣,销路却不佳。他写作的书籍包括两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其中一部显然是自传。
《伟大的圣战》(The Great Crusade )出版于 1940 年,讲的是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渐渐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要在两条战线上战斗:既要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作战,又要反对破坏共产主义事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小说篇幅很长,有时晦涩难懂,却是真情实意之作。其中一章有一个段落提到对忠诚的革命者而言,幻灭的过程何其痛苦。革命知识分子尼古拉·布哈林在1930 年代的清洗中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从此便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为何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逐渐变质的革命。但他的求索没有答案,只有“无尽黑暗的虚空”。
海明威或许没有逐页阅读过那部小说,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它隐含的意义,就停下自己的小说,为这部关于“国际纵队的黄金时代”的小说撰写了序言。他对雷格勒和第十二国际纵队赞誉有加,雷格勒曾在第十二纵队服役,海明威也常常到访。海明威写道,战争期间,那是他心灵的归属。纵队的战士们非常勇敢,几乎始终充满欢乐,因为那时他们认为共和国必将胜利,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海明威接着写道,在哈拉马河(Jarama River)附近的山坡上进行的“唯一一次十分愚蠢、计划和执行都毫无章法”的战斗令他愤愤不平,那次战斗大大削弱了该纵队的力量。计划和指挥战斗的那个人“后来在回到俄国后被枪决”,他对这一结局倒还满意。
海明威没有提到那位指挥官的姓名,但那想必是共产主义战士亚诺什·加利茨(Jaˊnos Gaˊlicz),海明威称他是一位厌恶新闻记者的匈牙利人,还说他“当时就该被枪毙”。海明威又一次让苏联人无功受赏,内务部不可能是因为加利茨无能而枪毙了他。相反,他之所以被枪毙,一定是因为他曾在西班牙服役,在斯大林偏执狂的观点看来,这足以把他变成一个可疑人物了。
在《伟大的圣战》的序言中,海明威还提到了苏德条约。他的观点与雷格勒大相径庭。德国人认为斯大林首先不该放弃西班牙共和国,更不该牺牲共产主义理想,跟希特勒签什么战术协议。海明威则相反,他愿意相信斯大林是好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时,苏联可没有跟希特勒签署任何条约。只有当他们(苏联人)丧失了对民主国家的信心,才产生了(苏德)盟约。”海明威对条约的支持让读者们大跌眼镜,看似断章取义的误读。但这确实是他当时的典型思维方式。他因为斯大林曾在 1936~1938 年支持共和国和国际纵队而向后者致敬,并坚称在慕尼黑协定之后,苏联独裁者为了自保而别无选择,外人无权为此对他横加指责。
雷格勒似乎了解好友的想法,他说海明威基本上是个“不懂政治”的人。跟政治比起来,欧内斯特倒是更了解丛林法则。他更像个猎人而非政治家;他看待问题“黑白分明”,要么生,要么死。他不明白“现代独裁者哪怕对童军法则也没有丝毫尊重”。同样,雷格勒曾在西班牙对一位更有同情心的苏联人说,海明威也不拥护西方民主,他赞同的生活方式,是在像非洲的高山或基韦斯特海域那样的地方最充分地体验生命。

斯大林
其后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令人眼花缭乱。9 月,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但对波兰的遭遇却无能为力;希特勒轻易便占领了倒霉的邻国,为斯大林根据两国的条约占领波兰东部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许多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目瞪口呆。11 月,斯大林入侵邻近的民主小国芬兰。那是一种旧式的武力抢地,跟沙皇或罗马皇帝的做法如出一辙。芬兰人像大卫对战歌利亚一样反抗入侵,战斗一直持续到 1940 年 3 月。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在重兵把守的法德边界与德国开战了。这就是 1939~1940 年冬天的所谓“虚假战争”(Phony War),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1940 年 5 月,当德军攻破了比利时境内林木茂密、看似难以逾越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时,虚假战争结束了。一队队坦克和机动部队包抄了边境的防御工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就突破了盟军的防线。希特勒用短短六周时间就占领了法国,把英国赶出了欧洲大陆。英国,这个因为没有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遭到海明威最多批评的国家,如今只能以一己之力对战轴心国,只能靠海外领地给予支持。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决心一战到底,但英国的前景却很糟糕。很多美国人怀疑它根本无法战胜希特勒,怀疑美国是否应该予以支持。盖尔霍恩就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英国似乎总算要为西班牙和捷克、波兰和芬兰付出代价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最初几个月,海明威仍在聚精会神地写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偶尔露面写几封信或关注一下盖尔霍恩。她在一封信中说他对待手稿“像一头动物”,要么把它紧抱在怀里,要么藏在抽屉里的其他文件下面。他从不愿意给任何人看,也不愿意谈论它。盖尔霍恩出发前往芬兰去报道苏联入侵时,海明威只是赞扬了她投身战争的过人胆识,却对苏联入侵邻国的行径只字不提,不止一位幻灭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颇有微词。
当他再次转而关注西线时,也只是再次对英国口诛笔伐。例如在 1940 年 5 月,他提醒麦克斯·珀金斯注意英国人曾经多么堕落。在西班牙,“(就在)我们不计回报地为他们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战斗时,他们却让我们陷入最大的麻烦,要知道只要他们给我们一点点援助,我们就能无限期地牵制住法西斯,令其动弹不得”。他预言说他们会卷入他所谓的“英式滥交”——也就是说,他们会从战场上撤军,对同盟弃之不顾。

电影《至暗时刻》剧照
欧洲发生的灾难刺激了海明威曾经的好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后者公开反对美国的中立态度。在1940 年春天的一系列谈话和文章中,刚刚被任命为国会图书馆馆长的麦克利什悲叹道,居然有这么多美国年轻人对战争持怀疑态度,几乎到了绥靖主义的地步。他认为这要归咎于那些反战小说,比如海明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永别了,武器》。海明威愤怒地回击,说麦克利什搞错了。德国人了解战略战术,盟军却一无所知,这跟反战小说可没什么关系。
麦克利什一定“心有不安”,而他海明威没有,他曾“在各条战线上与法西斯战斗”,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建议麦克利什读一读《第五纵队》(他那部关于不惧亲力亲为的反间谍的戏剧),再去观看一次《西班牙土地》(他们一起制作的纪录片)。他还略带挖苦地说起西班牙的前线,他曾亲自前往,而麦克利什却没有。三周后,海明威还在对麦克斯·珀金斯抱怨麦克利什,写道:“如今人们又是绝望崩溃又是歇斯底里又是宣泄怨气,我可不想再写什么呐喊助威的东西了。”
麦克利什选错了攻击目标。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伟大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事实上就是写全力以赴地面对战斗的。它与出版于 1929 年的《永别了,武器》全然不同。早期出版的那本书写的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爱情故事。战士弗里德里克·亨利把战争抛在脑后,因为一系列不幸的事件而被迫当了逃兵。他跟情人凯瑟琳·巴克莱一起逃往中立区瑞士。巴克莱怀孕了,世界缩小成为亨利和巴克莱周围的一个小圈子。孩子是死胎,巴克莱不久后也死于并发症。与之相反,关于西班牙那本书的书名就让读者去寻找故事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丧钟为谁而鸣”是约翰·多恩的诗句,那首诗开头第一句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
这部新小说以海明威与共产主义破坏分子打交道的经历为原型,讲述了一支在法西斯敌后行动的游击队为时四天的故事。他们的任务是在大进攻开始时炸掉一座桥,从而阻止法西斯的行动。美国游击队战士罗伯特·乔丹不但没有当逃兵,反而为反法西斯事业献出了生命。乔丹思想活跃,总是禁不住考虑自己怎么会如此沉迷于政治和战争。他知道战争为何而打,也知道该怎么打,跟海明威一样,他也相信共和国需要共产主义纪律,才能战胜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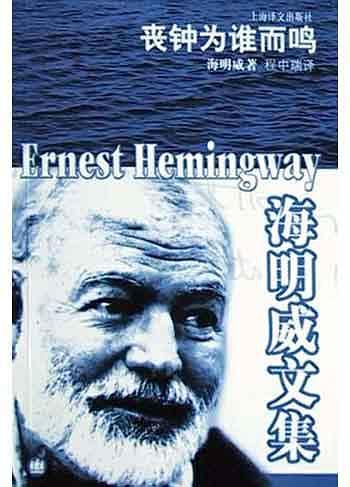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程中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在乔丹看来,共产主义纪律并非完美;只是它最符合当时的要求。乔丹自己也承认某些共产主义领袖凶残无能,他们的行为对战局的破坏不亚于法西斯探子。首恶就是法国人安德列·马蒂,也就是雷格勒跟海明威说起过的那位国际纵队总政委。海明威对自己描述的场景确信不疑,甚至都懒得在小说中掩盖马蒂的真实身份。
对乔丹来说,法西斯实施暴行是已知的事实,他们曾经轮奸了他的爱人玛丽亚就是一例。乔丹还知道共和军的记录也绝非无瑕。他就听说过一次暴行,不亚于战争期间发生在一个名为隆达的地方的事件。在小说中,占领那座小镇之后,共和军决定迫使它那些德高望重的镇民(他们要么真的是,要么被怀疑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从两排挥舞着木叉、连枷和镰刀的人中间走过。那些民族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带着些尊严而死,作者没有把他们大而化之地写成法西斯恶魔,而是着笔描述了个人的死亡。海明威对卡什金说,“我努力展现(战争)各个不同的侧面……让自己慢下来,诚实面对,从多个视角审视它”。
海明威不偏不倚的态度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赞赏。埃德蒙·威尔逊就赞美1937 年那个“佛罗里达饭店的斯大林主义者”海明威死去了,“艺术家海明威(又回来了)……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回来了一样”。然而这样的公正态度又让他失去了左派的朋友。曾一度做过西班牙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Julio Alvarez del Vayo)在 1940 年底读到《丧钟为谁而鸣》时,替许多人说出了心里话,他写道,海明威的书让他这样的流亡者感到“悲愤”,在他们看来,该书根本就没有抓住那场战争“你死我活”的真正本质。
美国共产党员阿尔瓦·贝西曾在战场上遇到海明威后将他引为知己,在他看来,此书不啻背叛,是对一项崇高事业的残忍曲解。贝西带着一丝遗憾为《新群众》撰文,称海明威本可以为这场人民战争写一本伟大的书,但他却掉入了个人主义的陷阱,以战争为背景写了“一部国际化的爱情故事”。
海明威把政委马蒂描写成“一个傻瓜、疯子和……杀人犯”尤其让贝西生气,攻击马蒂会让“我们共同的敌人”感到快意。贝西承认,海明威并非有意诽谤西班牙人民或苏联,但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却达到了那样的效果。“海明威表扬了单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英勇行为……(却)责难和中伤他们的领导能力、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其他评论家,如林肯营的指挥官、同是海明威好友的米尔顿·沃尔夫,责备这本书无视民族主义者犯下的暴行—— 就算说了也是轻描淡写,他强调,那些暴行是政策问题。
海明威在非洲
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有组织地杀人,而红军并没有。(或者至少程度不同。如果对内务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异见分子的运动忽略不计的话,这倒是真的。)尤里斯·伊文思最终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但他没有愤怒声讨。他会提出温和的判断,说海明威在写这部小说时,“回到了他原来的(非政治)视角”。
伊文思错了。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海明威。他曾经满怀激情地赞同共和国,反法西斯,而今仍然如此。1939 年唯一的改变,是他不再为了保护共和国而自我审查和删减了。他现在能够道出自己所见的全部真相,这是雷格勒等某些前共和军成员鼓励他做的。在战争中,雷格勒曾跟海明威分享过一些党的秘密,但作家没有利用那些材料,因为那时党还在为共和国而战,而共和国还有一线生机。只有当战争结束之后,他才可以尽情抨击那些破坏了革命事业的人。共产主义者们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亚伯拉罕·林肯营乃至由此类推的其他国际纵队成员,都“太关注意识形态,没有足够的训练、纪律或武器装备”。他们总是被那些无能的指挥官无谓地牺牲。
雷格勒断定,无数读者会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到教训,那些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学习的。凭借着猎手对偷猎者的憎恶,作家描述了“间谍病那些可耻的、凶残而愚蠢的运作,那是苏俄的梅毒”。人道主义政委雷格勒知道,强化革命纪律的方式有很多。就像他比喻中的猎手一样,他不反对杀戮,但他反对无证杀戮,认为那是违法的。雷格勒理性地确信海明威跟他想的一样。不到两年后,这个德国人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质疑海明威的判断了。
以上文章节选自《作家、水手、士兵、间谍》
文章来源:编辑 | 十六
| 上一篇: 开挂的复旦创始人!中国缺少一味药,名字就叫马相伯 |
| 下一篇: 罗马的富人与穷人 |